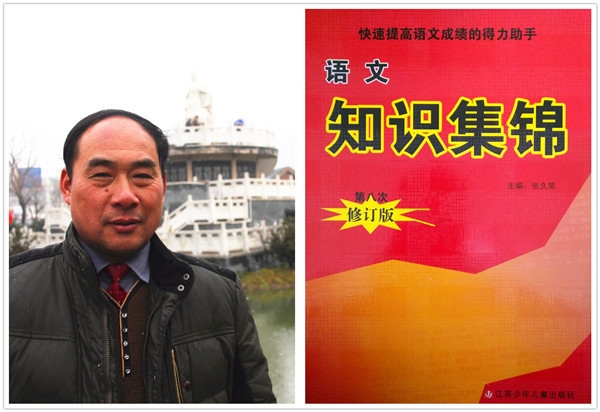|
大哥
作者:王兴业
救护车撕心裂肺地呜叫着驶入我家门口,侄子侄女把一个瘦得剩下六七十斤的老汉从车上抬下来,没等我仔细端祥,在司机的再三催促下,哥哥被匆匆放进了灵棚。
我的心剧裂地疼痛起来。哥哥一生劳碌,大半生在车上度过。当煤矿工人上下班坐拉煤猴儿车,一天两趟,二十多年从未中断,总里程可以绕地球几十圈。为省二块三火车票钱,扒着拉煤的火车从大同回朔县,冻得手脚流黄水。每次在矿上见到哥哥都是满脸黑煤,就能看见个白眼睛仁,张嘴说话时,才能见到口中带着煤灰的上下两排白牙。退休十几年了,每每吐出的痰里还带有黑煤灰。这次哥哥头一回享受轿车的高级待遇,却是他最后一次的旅行。父母一生与土坷垃打交道,穷得没个亲儿六人,唯一疼我亲我相依相伴的大哥没等我有个思想准备便撒手离开了骨肉二弟。走后他那张没牙的嘴张开着,怎按始终合不上去。我懂他的心思,他不想走,他没有完成我要求他活到八十岁的任务,七十八岁就急急地走了。
前两天他还给我打电话,说是出了医院,自已能下地送屎尿,叫我不用操心。我说你好好保养,不要抽烟喝酒了,他说酒不喝了,也不想喝,烟娃们不让抽,为了好出痰抽上三两口。我说过五一我去看你,他说来哇我想你。我说到了夏天回老家住上一段时间,我领上你看大秧歌,他说想看哩,不知道行不行。我说哥行,你怎也活大大个岁数,过个八十大寿,他说是哩。这才过了几天,我睡到半夜急醒,心崩崩的跳,坐起来一杯开水还没喝完,手机响了,侄子打来电话,说怕是不行了,我说赶紧度担哇,时间是凌晨四点半。
哥哥生于一九四零年农历九月初一子时,算命的说他命硬,一生劳苦发不了猛财。他不信邪,我当兵那年他招工去了煤矿。退休前在大同王村煤矿当工人,一直在条件十分艰苦的井下工作。开始到矿分配他在井上土建队当瓦工,他嫌挣得少,上有老下有小,一个个像张开嘴等吃食的雏燕,月月入不敷出。于是自已写申请主动要求入坑,到井下工作由二级工升到四级工还能多挣十几元入坑费夜班费,多挣一整袋白面。在阴冷潮湿黑洞洞的矿井里,他背着150斤重的建筑材料,踏着湿滑的台阶,下到八百米深的井下,再坐上运煤的猴儿车,从坑口到十几里远的工作面砌墙打封闭。背上比他还粗的木柱,半猫着腰行走在一米三高低的煤巷里,汗水和顶板上的淋水把破旧的工作服湿透干了,干了再湿透十几回。出井迟了,赶不上运煤的猴儿车,步行十几里出坑口。十几个小时的劳累,他饿过了头,进入洗澡池泡着,不知是睡了还是昏了。工友摇了几次才把他摇醒。别人用力气挣钱,哥哥瘦干的躯体在用命挣钱。年复一年,日复一日。在煤尘粉尘和劳累的双重折磨下,他有了肺部腰部严重疾病,退休后腰稚间盘突出变形,弯腰几乎九十度,成了个背锅老汉。我请遍了太原的专家名医土医生,吃药贴膏药牵引,折腾了七八年,好容易能直起腰走路了,又被食管炎肺气肿折磨,直到肺心病严重,几次走进了病危抢救室,我和二弟去医院看他,他头上插着一堆管子,心脏积水,生命垂危。原估计等春暖花开时应该会逐步好转,却不料和母亲一样在春草发芽乍暖还寒的暮春时节他倒下了。尸骨停放在黑布盖着的灵堂里,等到盖上棺盖把人封入那个木盒时,我终于控制不住情感,痛断肝肠的哭声从心里喷出,我一生相依为命的哥哥永远地离开了我,离开了他最不想离开的世界,侄子侄女哭得倒在棺材前面,后面的亲人们哭声震天。我的心剧烈地疼痛着,疼我亲我把我当儿女一样亲的哥哥撒手人寰,离我而去,怎不叫人泪如涌泉,痛彻心扉。当夜我睡在沙发上,眼睛盯着电视,一夜难以入眠,哥哥的音容面目难以拂去,儿时的往事一桩桩一件件地涌上心头。
我生在腊月初二黄昏时分,正是掌灯时节,哥哥放学回来,得知家里添了个小弟弟,急猴猴地要上炕看我。母亲让他拿个箩子过来,隔着箩眼看我,母亲说我哥九月初一出生命硬,哥哥脸靠近箩眼终于看清了眼晴和他一样大,眼睛仁一样黑的二弟,他知道这个比他小十一岁的弟弟,便是他最亲最近终生相依为命的手足。从那天起他和父母一起担起了养育我成人的义务,开始了相依为命的艰难人生。
哥哥结婚了,大叔赶上村里唯一的一辆牛轱辘车,到十几里外的木寨村娶我嫂嫂。我和姨哥穿上新衣服当伴郎,兴高彩烈地坐上牛车。牛车五更出发,走了三个小时的路程才到达了比我们村大好多的陌生村子,比我大九岁的如花似玉的嫂嫂抱着我上了牛车。从此家里多了一个一样亲我疼我的嫂嫂。十二岁母亲死后,哥嫂父母般地照料着我,和他们的四个子女一样亲我。我那时在师范附小上学,中午带干粮,哥哥把最好的粮食留下,嫂嫂变着法让我的干粮袋子装上玉米面高梁面屯屯,带上咸菜盐水,从兰瓶里困上几滴麻油。当时几十个跑校生中午在食堂溜饭,许多同学拿得是两个生山药蛋。考上朔县一中,报名通知书下来了,学费伙食费七块半。哥哥东家进西家出,终于凑够了天文数字般的七块半。嫂嫂把我的被褥拆洗的一干二净,哥哥背着被褥枕头送我进城,一直到我进入教室他才离开。一再叮咛我好好学习,再穷再难哥也供你上学。我每月伙食费七块半,有四块助学金,自已要缴三块半,哥哥拿不出来,蹲在街头把他最心爱的那双部队带回来翻毛皮鞋卖掉了,他苦笑着说,等二弟有了办法给我买哇。文革开始娃们都去串连,全国各地走,我也要去,哥不放心不想让我去,我背过脸哭了,哥哥赶紧从兜里掏出仅有的几块钱,果哄我别嚎了,路上听老师话小心走丢了。我没等说完,就兴奔奔地跑走了。长了这么大,哥哥嫂嫂没和我红过脸,没厾过我一指头。我也像孝敬父母一般地孝敬他们。六年前嫂嫂走了,今天哥哥也走了。从坟地回来,一股冷风吹来,吹得我冷到骨头里。侄儿侄女回了大同,家里只留下孤零零的我。没有了大哥我才发现我是那么孤单,孤单到欲哭无泪。
安息吧,我的大哥。
二O一七年五月二日凌晨四点半
|

 手机版
手机版